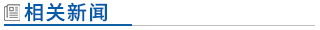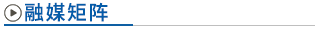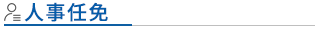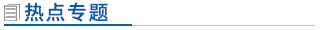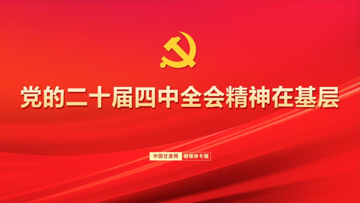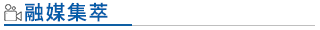人到中年,愈發孤獨,不是被別人孤立,而是內心感到孤獨。索性把時間還給自己,把美好的孤獨留給自己,有種“畫地為牢”的喜悅。那些說不著的,不屑去說;說不明的,不愿去辯,連看一眼都覺得是過錯。
這樣的體驗,很契合劉震云《一句頂一萬句》中人物的心理,也是我深愛此書的一個很特別的理由。想起小說里的老范雇用老汪做私塾先生,不是因為老汪講得有多好,而是他嘴笨,老范腦子又慢。一個嘴笨,一個腦子慢,“腦與嘴恰好能跟上”。
閱讀是一種體驗,一個人生命中的切身體驗能與一本書契合,我想可能更是一種幸福,如同世間又多了一個知己。當我再次捧讀這部小說時,似乎不是小說人物在說話,而是他們在替我發聲。把我想說的、不能說的、不敢說的、說不明的、說不透的,都說了出來。有的共鳴在預料之中,有的啟迪當然也就在預料之外了。
劉震云的文字煙火氣濃郁,說的是平常百姓的話,又非平常百姓的味。他筆下的人物都長了一條如簧的巧舌,更難得的是,他的書寫又兼具口語與書面語,實現了深度的融合。其中,“不是而是”這一并列復句結構,在他筆下突破了原有的定式,實現了饒有趣味的創新。劉震云將其拓展為多重嵌套、交叉、疊加的句式,讓單一簡短的句式發展成跌宕起伏的故事段落,猶如一條路,折來繞去,蜿蜒成豐滿的篇章。
如此一來,在這些創新的句式中,兩個聯結詞之間不再是簡單的否定與轉折,而是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否定、轉折、否定。從這樣的嵌套中,我們得以窺見生命的無常、戲謔、荒誕,那些偶然的邂逅,那些意外的巧合,那些說得著的、說不著的,以及命運深處不可抗拒的因素,都被囊括其中。
仔細想來,這種獨特的“句式”結構,超越了語法范疇,已經構建了小說故事的框架。忽然想起“芥子納須彌”來,一句簡短的平常話,靜水流深,暗藏波濤洶涌,它可以是一段人生故事、一幕生活場景、一次命運轉折,等等。劉震云精心書寫這些蘊含哲理的故事、人生感悟,讓簡單的“不是而是”煥發新生,讓一截枝丫成長為一棵蓊郁的大樹,形成獨具個人特色的語言美學。
依我之見,除了構建故事的框架,這種語言結構與敘事形式,將節奏與韻律巧妙地轉化為讀者的閱讀節拍。閱讀之人,仿佛肩上落有一副擔子,音樂響起,每一步都踩在節拍上,一步一步,在作家設定的語言韻律的道路上行走,不顯得遠,也消遣了累。這種由語言敘事節奏帶來的沉浸式閱讀體驗,給予閱讀的愉悅不言而喻。
或許,其中也包含作家的另一層深義。作家如此不厭其煩且樂在其中地書寫“不是而是”,想來很像小說人物蕓蕓眾生的命運,出延津,回延津,執著到近乎固執、一根筋。劉震云用文字繪制了一幅中原大地的《清明上河圖》,畫卷鋪展綿延百年,人物熙攘往來不絕,好不熱鬧。小說的上半部主人公楊百順,名為百順,其實百無一順,先后磨過豆腐、殺過豬、挑過水、燒過火、種過菜、蒸過饅頭等。可作家還覺得不夠深入,于是楊百順又改名楊摩西、吳摩西,也在茫然失措中叫過喊喪的羅長禮,后來真就叫了羅長禮,直到終老。這一切的目的很明顯,就是改頭換面,徹底和自己的不堪過去告別、決裂,然而事與愿違,生活的軌跡始終徘徊在“不是而是”的悖論中。下半部主人公牛愛國依然尋找自己“說得著”的人,這種精神的契合,即便找到了,也被現實的戲謔當成一種玩笑。正如作家借用曹青娥的口說出:別的東西都可以挑,就是日子沒法挑。他們苦苦尋找,其實就已經證明,世上根本就沒有與自己思想行為完全契合的人,沒有純粹能“說得著”的人,在人的一生中,有那么一段時間能“說得著”,或相濡以沫,就已經夠幸福了。劉震云的“不是而是”的句法,其實就是小說人物蕓蕓眾生的命運之隱喻。楊百順(牛愛國)不屈服命運的束縛,執著出走傷心地。對于他們來說,只有這樣才能告別過去,奔向新的未知,新的未知中或許就有他們尋找的幸福。
如果說《清明上河圖》是畫出了形與貌,那么《一句頂一萬句》就是寫出了神與魂。
倘若把劉震云的小說與遲子建《額爾古納河右岸》來對比,遲子建的文筆更像靈動且憂郁的蝴蝶,而《一句頂一萬句》是一幅碩大的蒼生百態黑白素描畫,以老辣的筆觸、強烈的反差、詼諧的色調、直抵人心的力量,迫使讀者停下閱讀,深入思考。停下來思考的不是故事,而是那些戲謔驚悚的語言,和背后的種種辛酸。
小說語言平白,是平中有奇崛,白中見色彩,到底是蘊藏著催人淚下的生活百般滋味和人間最柔軟的溫度。
語言是思想的載體,文學作品是借助語言來構建一個虛實相生的世界。汪曾祺言:寫小說就是寫語言。可見小說語言的重要性。相較于炫目華麗的辭藻,風格平白樸實的語言往往更能叩擊大眾心靈,引發情感共鳴。這種語言又不同于詩歌,詩歌講究“語不驚人死不休”“吟安一個字,捻斷數莖須”的極致追求。然而,面對長篇小說《一句頂一萬句》,這種字字推敲的創作方式顯然難以實現。小說的魅力,在于通過看似平常的語言書寫出市井煙火的蒼生百態。小說語言看似平白、自然、樸素,其實每一句都浸潤著深厚的個體生命體驗,回味雋永而挹之不盡。
活了70歲的曹青娥那句“過日子是過以后,不是過從前”,道出了生活的真諦。當人們都趨向“活在當下”時,作家卻借這句樸素的話語,道出拒絕精神內耗、放下過往的人生智慧,只有這樣,生命才能一往無前。我們再揣摩這一經典句子,“世上別的東西都能挑,就是日子不能挑”,看似在說生活的無奈,其實是揭示出命運的荒誕。每個人都在柴米油鹽的瑣碎中被動前行,在拆東墻補西墻的物質與精神的困境里掙扎,面對疾病災禍,更顯得渺小無助。
劉震云對生活細節的敏銳捕捉,賦予小說直擊人心的力量。他寫道:“與人說話,沒開口先笑;同樣一句話,兩種說法,她揀的是好聽的那一面,壞話也讓她說成了好話。”寥寥數語,道盡說話的微妙與復雜,每一句,讀它的人都能對號入座,找到自己的過往故事與心酸經歷。作家將語言背后的人性剖析得淋漓盡致,極為深邃。說話的人重要的似乎不是說了什么,而是說話這種行為本身所塑造的一種定勢。即便是表面的、流于形式的思考姿態,也足以固化一個人的良好印象。可以說,這些看似平實卻飽含生存智慧與隱憂的文字,每一句都是作家個體生命體驗凝練而成的生活哲學,這不只是一個作家的敏銳與感懷,更是偉大人格力量和深沉之愛的一種體現。
正如賈平凹在雜文《說話》中對語言藝術的入情入理的闡釋,劉震云的小說同樣充滿思辨色彩。那些或直白或繞口的敘述,藏著對人性的深刻洞察。“同樣是一件事,對自己有利沒利他不管,看到對別人有利,他就覺得吃了虧”,這樣真實又微妙的心理刻畫,讓讀者在共鳴中反省自己,揭示社會暗藏的運行規則,以及人性之丑陋。
《一句頂一萬句》給予我們的是:文學的力量不在于晦澀難懂的大道理,而是將平凡生活中的細微洞察,轉化為穿透人心的真知灼見。“世事洞明皆學問,人情練達即文章”,那些源于生活、扎根現實的文字,才是小說最動人的魂魄。
- 2025-11-17第四屆“陳伯吹新兒童文學創作大賽”頒獎典禮舉行
- 2025-11-13《玉壺僑史札記》新書首發式暨僑鄉文化座談會舉辦
- 2025-11-13廣播敞開文學傳播新空間
- 2025-11-13紀念鄒韜奮誕辰130周年 “韜奮好書”“好書評”揭曉

 西北角
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微信
中國甘肅網微信 微博甘肅
微博甘肅 學習強國
學習強國 今日頭條號
今日頭條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