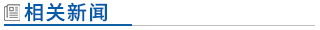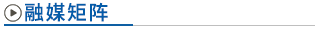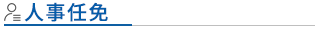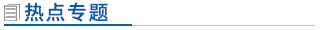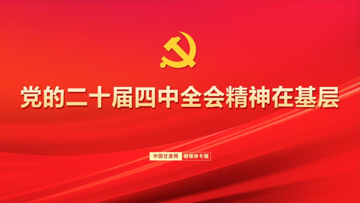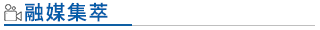初秋時分,市民在銀杏樹下拍照打卡

深秋的蘭州,一條條“黃金大道”在社交媒體上刷屏。蘭州理工大校園、甘南路、西固東路等地,銀杏樹編織的金色穹頂下,擠滿了拍照打卡的市民。然而,這幕城市盛景背后,藏著一個違反公眾直覺的科學事實:這些看似繁盛的銀杏,在《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》上,赫然標注著“瀕危”(EN)二字,與中國大熊貓同級。
一邊是城市里“滿城盡帶黃金甲”的觀賞盛景,一邊是物種名錄上觸目驚心的“瀕危”標簽。這背后,是一場持續了數千萬年的生存史詩,一個關于演化、庇護與孤立的現代悖論。
金色大道!
精心呵護出來的繁榮表象
“在蘭州,銀杏確實很常見,但這只是一種表象。”蘭州市園林科學研究所所長許宏剛指出,“我們看到的都是人工栽培的個體,而非自然繁殖的,它們就像被復制的同一張光盤,缺乏遺傳多樣性,是一種高度人工化、精心管理的‘繁榮’。由于它們的野生種群或者自然條件下的個體數量稀少,科學家依據它們的野外分布狀況,把它們評為瀕危植物。”
從生物學角度講,瀕危說的是植物在野外環境的生存狀況,不包括街道、小區里人工栽培的那些植物。許宏剛解釋道,銀杏是雌雄異株植物,但城市綠化出于精細化管理的需要,有著明確的“性別篩選”。“為了杜絕成熟白果掉落產生的異味和污染,我們在街道綠化中普遍選育雄株,或通過嫁接技術控制性別。這意味著,整條街上的銀杏,可能源自極其有限的幾個無性系母本,遺傳背景高度同質化。”
這支規模龐大的“景觀兵團”,雖然構成了壯麗的城市風景,卻在生物學上陷入了困境。“它們是被精心呵護的‘盆景’,彼此之間無法通過花粉與種子的自然交流產生新的遺傳組合。它們的生命延續依賴人工扦插與嫁接,這是一種靜態的、停滯的繁榮,喪失了在自然環境中通過有性繁殖來適應未來環境變化的進化能力。”
野生種群:
深山“孤島”與城市“真空”下的生存警報
城市的金色繁華,反襯出物種在原生境地的深刻危機。一個關鍵且常被忽略的事實是:根據蘭州市林業和草原局的全面調查,在全市域范圍內,目前未發現任何野生狀態的銀杏樹。這片生態上的“真空”,并非特例,而是全球銀杏野生種群現狀的一個縮影。
“IUCN(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的簡稱)的‘瀕危’評級,其評估對象嚴格限定于野生種群,而非人工栽培個體。”許宏剛再三強調這一國際通行的評估標準。目前,科學界公認的真正野生銀杏,僅如“孤島”般殘存于中國浙江西部的天目山、湖北的大別山和神農架等極少數在第四紀冰川期中的“生態避難所”。
“這些‘孤島’彼此隔絕,種群內部個體稀少,加上雌雄異株導致的‘生殖隔離’,使它們的自然更新率極低。”許宏剛描述了一幅艱難的野外圖景,“你可能找到一株百年的野生雌樹,但如果數公里內沒有一株雄樹為其傳粉,它就無法留下后代。這種‘相見時難’的困境,是導致野生種群持續萎縮的內在原因。”
此外,由于目前種植銀杏的基因不再具有多樣性,所以一旦自然界暴發一場針對銀杏的疫病,可能所有的銀杏樹都會因病毒感染而死亡。
演化盡頭?
“活化石”的基因危機與古樹的警示
中國不僅是銀杏的故鄉,而且也是栽培、利用和研究銀杏最早、成果最豐富的國家。古往今來,無論是銀杏栽培面積,還是銀杏產量,中國均居世界首位。從現存古銀杏樹的樹齡來看,中國商、周之間即有銀杏栽植。
許宏剛介紹,在甘肅省隴南市徽縣銀杏村,銀杏樹的栽植歷史超3000年,千年以上古銀杏樹有42株,形成全國罕見的古銀杏樹群落。在天水市秦州區青年南北路兩旁種滿銀杏樹,深秋時節形成一條金黃色的“黃金大道”,已經成了著名的旅游打卡地。
相比之下,蘭州街頭樹齡多在10年至15年的行道樹,與全市范圍內僅有的4棵被掛牌保護的銀杏古樹形成了意味深長的對比。據文獻記載與普查確認數據:雁南路、天水路沿線存有2棵樹齡約120年的古銀杏樹,此外,蘭州大學校園內還有2棵約100年的古銀杏樹。
“這些歷經世紀風雨的古樹,是活著的城市編年史。它們所承載的地方記憶和生態歷史,與深山野生種群所承載的遺傳信息一樣,都是獨一無二、不可復制的珍貴遺產。”許宏剛說。
“銀杏在蘭州需要額外呵護。”蘭州市林業和草原局城市園林綠化科科長成曦坦言,“夏季需要定期澆水,冬季又要防寒保護。它們能存活,更多的是依賴人工干預。”據介紹,截至目前,蘭州市在甘南路、西固東路、安寧532號路、572號路、西固東西路、雁北路、麥積山路等12條城市主干道上,共栽植了2506棵銀杏樹作為行道樹,這還不包括散布在各公園、小區內的數量。可以說,銀杏已是蘭州城市綠化中不可或缺的骨干樹種。
展望未來:
城市綠化可嘗試為“活化石”提供一絲演化的生機
既然人類已能通過無性繁殖技術大量“復制”銀杏,為何還要不惜代價地去保護那些深山中瀕危的野生種群?許宏剛剖析說:“其一,野生種群在漫長的自然選擇中,可能蘊藏著對抗某種未知致命病害、耐受更極端干旱或高溫的‘求生密碼’,這些潛在基因是人工栽培樹種無法提供的。其二,銀杏是連接恐龍時代與今日世界的唯一植物橋梁。它的形態、生理和基因序列,是一部記錄了數億年地球環境變遷的‘活檔案’,其科研價值遠超任何化石。其三,保護野生銀杏,從來不是只保護這一棵樹,而是保護它以之為核心所形成的整個森林生態群落——包括與之共生的土壤微生物、傳粉昆蟲、伴生植物等,這是一個完整的生命網絡。”
許宏剛認為,未來的城市綠化不應止步于創造視覺美景,更可以嘗試為這些“活化石”提供一絲演化的生機。“例如,在公園、植物園或一些非核心路段,我們可以有意識地引入和栽植來自不同野生種群來源的銀杏實生苗,增加城市銀杏基因庫的多樣性。甚至可以規劃建設小片能夠自然授粉結實的銀杏林,讓它們在城市中也能完成生命的自然循環。”他表示,這或許能為在人工庇護下生存了千百年的“活化石”開辟一條新的生存路徑。
記者 譚安麗 文/圖
- 2025-11-17甘肅文旅推介會在巴黎舉辦
- 2025-11-17提供多元文化體驗讓書香融入日常生活 西固區打造“15分鐘閱讀圈”年服務讀者超76萬人次
- 2025-11-17讓每一個生命都享有尊嚴和夢想
- 2025-11-17甘肅省西部計劃赴西藏服務志愿者出征

 西北角
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微信
中國甘肅網微信 微博甘肅
微博甘肅 學習強國
學習強國 今日頭條號
今日頭條號